2016 年,初夏,我在印度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考察。
在结束考察回国后的第二天,我眼珠发黄,母亲问是不是肝出了问题?那时我已有一段时间腹痛,本以为是在印度吃坏了肚子,(还去当地医院开了药)回国养养肠胃即可,但母亲的警惕让我迅速去医院检查肝功能。
结果,我的转氨酶指标已超过 2,000(正常人也就在 15~40 之间),到了要命的程度,最终我被诊断为由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急性肝功能衰竭。
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医院下发了病重通知书,我的病床也被挂牌为一级护理。我问这什么意思,护士一边扎针一边说,「我们一个小时巡视一次,你要是不见了,我们就报警。」
因为这种病毒在中国不常见,但在南亚曾多次爆发,造成大面积死亡。医生说,从受感染到爆发通常有两周的潜伏期,因此可以推断为我是 7 月 10 日左右接触了感染源——通常在食物与水当中。
在诊断中,我向医生出示了我在印度服用过的药品,结果医生拿着我的药眯着眼睛看了看,说「吃错了,这些抗生素只会加重你的状况。」
就这样,我有机会在电脑前整理记录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得先以一个病人的身份讲述我在印度的日子。
挂号费 60 的私立医院 我在印度的行程是德里——加尔各答——德里。
在加尔各答的第二天晚上就出现了腹泻,那时并不确定原因——食物中毒、空调病,还是所谓水土不服都已经无从排查了。
那一晚我狠心把空调关了,三十七八度的温度下肚子又闹腾起来,再翻身下床,这样来回了 9 次,直到感觉自己已被排空。第二天醒来,身体消停了些,却完全不敢出门。
腹泻来势迅猛,上街临时找厕所显然不现实。无奈,我只能在旅社里呆着看点书,依旧不敢吹空调,只能把椅子搬到楼道口,至少有一星半点的凉意。当日下午,我恢复正常。
没过几天,强腹泻再次来临,和上次的情况非常相似,我决定暂时不吃任何现做的食物。
次日下午,我到超市购买包装好的食品。在超市里,难受的感觉又开始爬上来,最开始只是催着我赶紧结账走人,等我开始排队时,症状越来越严重,开始浑身无力,呼吸短促,好像失去了把空气吸进肺里的能力,听力也模糊起来,像是把头埋在水下一样,眼前的色彩也在涣散,只觉人影幢幢。
我明显站不稳了,能感到自己在一阵阵冒汗,只能把双手撑在柜台上不让自己滑倒地上,当时我一定有着愁苦的面容。
我用余光粗粗扫视周围,确定了一块空地,心想如果要晕倒,也要撑到那块空地上。
我不记得我怎样完成了结账,我终究没有一头栽下去,那么我要火速去急诊!我拿着饼干飘向超市门口,问保安,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一个旁人凑过来带有些许关心的神色说:「Ruby Hostpital,take a taxi。」我不停地重复念到 Ruby hospital,Ruby hospital, 靠着肌肉记忆死死地将这名字锁在嘴上。
超市外的路口正值红灯,停着的第二辆车就是辆出租车。我昏天黑地走了十米,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地往里爬,「Ruby Hospital!」
车开动了一会儿,我逐渐缓过神来,痛苦在我身上消散的过程无比幸福。我这时才能看清手臂上的硕大而密集的汗珠,像刚冲了淋浴一般。
司机将我带到一个像小镇的地方,一簇楼房毫无规矩地并在一起,我看见了医院高耸的牌子。
医院规模不大,但很新,地上有整齐的瓷砖,墙体的材质风格和走廊上座椅的风格与时下中国地级城市的医院相差无几,每个诊室门口有显示排队号的屏幕。
我上前挂号,需要缴纳 600 卢比(约合人民币 60 元)的挂号费。随后让我坐在椅子上排队,因为医生外出吃饭了。
我坐下来仔细打量周围,再想起那个告诉我 Ruby Hospital 的路人的脸,他体格健硕,肤色偏白,穿着 polo 衫,他应该是个婆罗门,是个有钱人,这家医院应该是私立医院,难怪建得那么远,很多来看病的人估计都是自己开车来。
我是医生的第二个病患。
医生是个唇上有胡须的中年男子,蓝紫色衬衣,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他对一个外国人的造访很感兴趣,跟我聊了不少,还提到他可能进行的中国旅行。
我躺在一张小床上,他用手挤压我的腹部(脏器)问痛感。医生最后说没事,我给你开点药随便吃点就好了。接着我领了 8 卢比(0.8 元人民币)的药品。
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 到了 7 月 17、18 号时,我开始感到轻微腹痛,把躯干挺直时,这种疼痛尤为明显。 腹痛的同时食欲下降,到后来我每天只能吃一顿,伴随多次干呕。我只能取消了去孟买的行程,在德里达旅社里看书休息,足不出户。
在旅社前台的指点下,我去了一家步行可达的公立医院 Palika Health Complex。由于我的旅社在德里使馆区,这家医院并没有人满为患——那是普通印度公立医院常见的景象。
医院的门诊楼如小学教学楼大小,虽不豪华,但也干净明快。我走到挂号处递给他们护照,他们竟表示不用,只递出来一张表,让我填完个人信息便可直接上楼候诊了。
诊室在三楼,六七个患者站在门口排队。由于腹痛导致站立难受,我想坐到旁边的椅子上,但是担心后来者加塞儿,只好勉力站着,上身前倾。
「Nothing serious」,「你们外国人来都会有这毛病,我给你开点药就好了」,说完医生敲了几下键盘,立方体一样的纯平显示器上跳出几行字。「好了,你拿到一楼去拿药吧。」
两盒药很快就从窗口里被扔了出来。在我拿起它们转身走出医院的那一刻,我一个外国人,不需要缴费也不需要出示证件,一次看病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免费医疗。
印度的免费医疗带给我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误诊,医生开的药反而加重了我的病情。我实在不知这是不是特殊情况。父母一方面责备印度医生误诊,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还好我没有在印度住院治疗,否则也许风险会更大。
公平与效率的角力 对印度的免费医疗,叫好者有,也有批评者认为,「那就是个笑话」。 在印度,公立医院的医疗条件和设备非常恶劣,手术的等待时间跨年是寻常事。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印度的有钱人都是去收费的私立医院看病,公立医院的设备差工资低导致招不到好医生,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用止泻药应对几乎所有前来就诊的病人。 根据 2015 年 WHO 公布的全球各国平均寿命,当时的印度平均寿命 68.5 岁,而中国平均为 76.1 岁。 2012 年,印度的医疗卫生投入仅占 GDP 的不到 1%,(2012 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占 GDP 的比例超过 5%,至 2017 年,官方公布的这个比例为 6.2%,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会超过 8%),且位列全球人均医疗投入最低的国家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政府还是决定在原有的免费医疗基础上,制定了一项全民免费拿药的医改计划,当然,免费药物的政府采购名单中几乎不包含任何进口药物或贵价药物。
还有一种评价认为,印度有着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因为特殊的专利管理制度,发达的仿制药产业令这个国家成了国际医疗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另一方面,因为设备落后的公立医院所提供的糟糕的医疗质量,几乎不含任何「高级」药物的免费药物列表,面对大病,免费的公立医疗与「无医无药」几乎差别不大。
而在另一些评价中,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评估排行榜上,印度的全球排名为 43 位,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公共卫生体系运作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始终是核心问题。
而在医药产业日渐壮大,医疗账单年年攀升的今天,如何使用有限的投入,让穷人既不会因为负担不起高额账单而放弃治疗,也不会因为医生的水平问题而不能得到应得的治疗,让医疗服务至少够用,目前中国抑或是任何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会比印度好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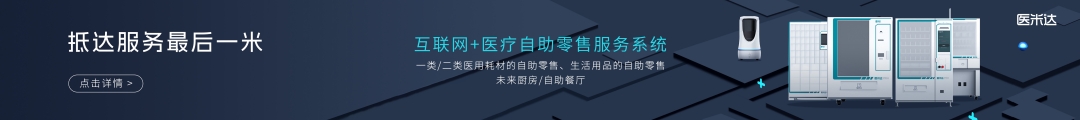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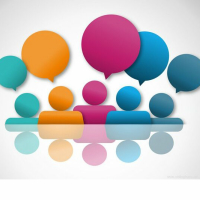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