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2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提请审议。草案中,“两禁止”引发热议,被视为“大转变”之举。
一是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二是禁止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与其他组织合作投资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关于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禁令从未解除,草案的意义在于将以往七零八落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博嘉并没有从中看到大转变之规定。相反,赵博嘉坚信,未来几年,这一禁令也不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正如约印医疗基金执行董事董迷芳所言,政府立法的初衷是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使其不被过度商业化。“很多社会资本打着与公立医院合作的旗帜,以建分院等形式,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种行为正是政府禁止的。”
媒体关于“两禁止”的报道一出,广东省卫计委原巡视员廖新波随即刊文称,“这些规定都不是新现象,但由于相关部门没有落实好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机制,使得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各自理解新政。”廖新波断言,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之日,方是社会资本办医成功之时。

广东省卫计委原巡视员廖新波
被忽视的禁令
禁止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政策由来已久。2000年,原卫生部出台《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投资与其他组织合资合作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
2012年6月29日,原卫生部下发《关于有序开展部分公立医院改制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社会资本以合资、合作方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的,不得改变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
尽管已有政策对双方合作进行过明确规定,但仍然不乏相关案例出现。资料显示,北京天坛普华医院是由北京天坛医院与美国医疗集团出资组建的营利性专科医院;新世纪儿童医院是由北京儿童医院与北京创巨科技公司共同创办的营利性专科医院⋯⋯
“已经出现的此类机构大部分立项较早,或许是在文件出台之前已经获批通过的。”赵博嘉告诉健康界,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国家就没有开过口子,“不乏个别地方存在审批通过的特例。”
社会资本希望能够借势公立医院的品牌优势,公立医院渴望吸纳社会资本的资金助力发展,往往双方一拍即合,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建新院,成为合作的首选模式。社会资本追求投资高回报比的天然属性,使得其倾向于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正如董迷芳所言,公立医院若想回归公益性,这一途径势必无法被国家认可。 试想,一家民营医院,或者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建的营利性医院,在其名称中,如果能够体现大型公立医院的名字,多少患者会趋之若鹜?“这种品牌效应所吸引的客流,是一家民营医院付出十几年的努力,都很难企及的口碑效应。”董迷芳的话,无疑道出了这一新政对社会资本的冲击。 同样,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项目一旦停止,其资金压力将急剧增加。据行业数据分析,湖北某三甲公立医院的人力成本占业务总成本从2012年的20.8%上升到2014年的40%;而财政投入在人力成本上的占比则从2012年的38%缩减为2014年的15%。众所周知,医务人员的奖金来源主要是医院的服务及合作项目创收。一旦合作项目被禁止,医务人员的薪酬将首先受到冲击。 在董迷芳看来,国家希望禁止的是公私合办营利性医疗机构等破坏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行为,“这种合作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会造成公立医院患者流失,使公立医院逐渐背离公益性”但并非所有的公私合作模式均被“一棒子打死”。 被模糊的概念 2017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在人才、管理、服务、技术、品牌等方面建立协议合作关系,支持社会力量办好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 “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的合作,与社会资本和公立医院合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完全不同。”赵博嘉强调,与此前的政策氛围相比,目前,只要采取国家允许的模式,公私是可以合作的,或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新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或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之间以签署协议的形式,开展人才、学科等方面的合作。 但董迷芳却认为,对于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仍然存在诸多模糊地带。“魏则西事件”后,国家对公立医院科室外包进行了严厉打击。“但何为科室外包,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董迷芳建议,从业者可以从人、财、物三个方面,判断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是否为科室承包。如果科室人员隶属关系在医院,科室医疗服务收费、人员薪酬绩效等与财务相关的事务归属于医院,科室设备等硬件设施同样归医院所有,社会资本提供的是不涉及人、财、物之外的服务,就不能被视为科室承包。 “公立医院无法对全民健康大包大揽,社会资本显然是公立医院最强有力的补充。”董迷芳补充道,公建民营、特许经营等概念同样存在模糊地带。托管协议签署程度如何、管理运营权力分配归属等,都可以从人、财、物方面加以界定。 对此,廖新波建议,公私合营要依法行事,社会资本不要过度依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有自己的办院宗旨,但这个宗旨来自政府部门,不代表院长或者投资者的意愿。”廖新波表示,部分社会资本希望“借船出海”,但随着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回归,其盈利空间将收窄,民营医院很难继续从公立医院挣回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资本赋能基层公立医院”这一观念被多位业内人士认可。董迷芳解释道,公立医院,尤其是基层公立医院在资金、设备等方面存在天然短板,但其又必须承担“90%大病不出县”、科学研究等重任。如果县级公立医院依靠有限的财政投入与自身“造血”仍旧难以顺畅运转,这无疑为社会资本留下了空间。 “社会资本可以向公立医院输入医疗设备、资金等硬件设施,但不介入科室及医院的人、财、物,并合理收取一定的咨询管理费用。“董迷芳认为,只要科学界定,社会资本将成为公立医院职能疏解的“助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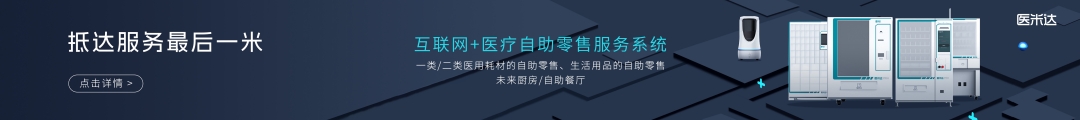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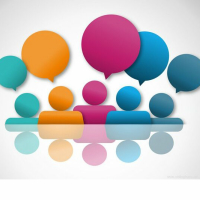 >
>







